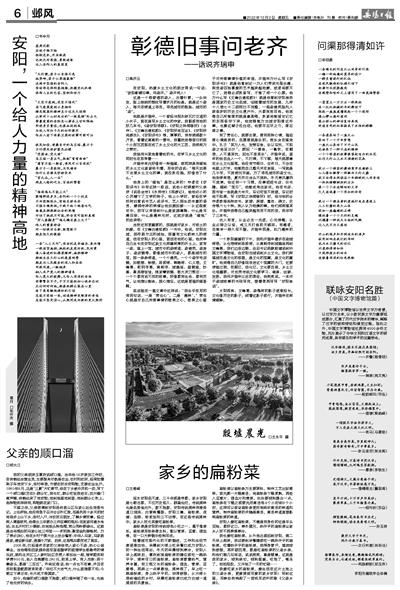□高庆云
在安阳,热爱乡土文化的朋友常说一句话:“欲知彰德旧事,问老齐。”老齐何人?
这是一个极普通的老人,衣着朴素,一头华发,脸上细细的皱纹写着岁月的沧桑。就是这个老人,每天在街道上寻觅,寻觅城市的根脉、城市的“老”。
他就是齐瑞申,一个曾经与泥水砖瓦打交道的小伙子,现在是写乡土文化的作家。我眼前有他的好几本书,《老安阳寻踪》、《安阳之洪洞移民》(合作)、《文峰古建悠韵》、《安阳民间百业》、《安阳民间游戏》、《安阳评书》等,厚厚的,洋洋洒洒数十万言。看着这高高的一摞书,我蓦然觉得昔日的那个小泥瓦匠现在成了乡土文化的大工匠。我深深为之赞叹。
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书,在学习乡土文化的同时也在思考着……
齐瑞申体内好像有一种强磁,被同样具有磁性的乡土文化紧紧吸引着。用他的话说:“每天如果不去做乡土文化的事,就没抓没挠,好像丢了什么。”
他身上的“磁性”是怎么来的?作者在《安阳评书》中有这样一段话,说他小时候爱听父亲讲《说岳全传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,给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他上小学时,曾经在学校附近看说书艺人说评书,艺人那生动丰富的语言、潇洒传神的表演让他如痴如醉……从这些叙述中,我可以体悟到什么是家庭熏陶、什么是耳濡目染、什么是趣味无穷,这或许就是“磁性”的由来吧!
当然还有更重要的,那就是对家乡、对故土的热爱。在《文峰古建悠韵》一书中,他说,安阳古城,那布局方正的城池,那富有文化韵味儿的街道,活在安阳人的心里,更活在他的心里。他庆幸自己生长在安阳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上。家有一老,堂上一宝。城市中的老街道、老建筑、老房子、老店铺等,都像城市中的老人,都是城市的宝。那一条条街道,一个个建筑,一个个老字号店铺,如鼓楼、钟楼,县前街、御路街、仁义巷,文峰塔、乾明寺塔,高阁寺、城隍庙、昼锦堂,妙真、聚宾楼饭馆,姚家膏药铺、杨大庆刀剪庄……一个个都有说不完的故事,好像都有生命、都有灵气,让他难以割舍,挂心难忘。这或是更强的磁场啊。
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:“我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,一是‘责任心’,二是‘趣味’。”责任心就是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敬畏之心。敬畏之心源于对所做事情价值的体悟。齐瑞申为什么写《安阳评书》?就是他看到这一为人们带来无限乐趣、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越来越枯萎,或者将要灭亡了,觉得必须抓紧写,才能了却一个心愿。他为什么写《文峰古建悠韵》?就是他看到安阳虽然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但随着城市的发展,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已不完整,一些老建筑除列入被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外,大都岌岌可危。他觉得自己所能做的就是拿起笔,抓紧将能留住记忆的东西保存下来。他觉得能为古城安阳做这件事,也算这辈子没白活。他要尽应尽之力,做应做之事。
有了责任心,就要去做。做有两种心情,强迫做心情是苦的,自愿做就是乐的。苦乐全在感觉中。孔子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;颜回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。齐瑞申说,退休的他自由人一个,不打牌,不下棋,每天就愿意在乡土文化里混。他没有节假日、双休日,不会在电脑上打字。他能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里,一写就是几千字,不觉背沉手麻。为了寻觅城市的老文化,他走街串巷,夏天烈日当头不觉热,冬天寒风凛冽不觉寒。他还有一个习惯,没事逛逛书店、旧书摊。碰到“宝贝”,他能成兜往家买。他在书店、图书馆一坐就是大半天,忘记吃饭不觉饿,忘记时间不知黑。写《安阳之洪洞移民》时,他与他的合作者参阅各种志书、家谱、族谱、墓志、碑文、史传等六七十种。别人认为枯燥的事,他们却深感其乐。齐瑞申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用不完的劲,两年写了三本书。
古人有言,从业必主一无适,心无旁骛;从业必持之以恒,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有趣者,自能专一持久而不辍。齐瑞申即是,此乃趣味的力量。
一个秋阳暖暖的下午,我和齐瑞申漫步在老城街巷,从仓巷街到县前街,从高阁寺到城隍庙再到文峰塔。我们边走边聊,由总书记视察殷墟说到中国文字博物馆,由安阳古城说到乡土文化。我们深感城市是文化的容器,是文化的宝藏,是文化的富矿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刚走进这个宝藏的大门,还要穿堂过院,挖掘它,活化它。文化要自信,乡土文化很重要。对优秀传统文化要学习、继承、创新、发扬。我问齐瑞申以后的想法,他笑笑说,一本关于老城故事的书刚写完,接着想再写写“安阳食话”。
太阳西斜,文峰塔、老槐树的影子逐渐拉长。文化像历史的影子,顺着这影子前行,齐瑞申在深情凝眸。